阿根廷圣克鲁斯省的平图拉斯河手洞,被列为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。人类来到美洲是走出非洲的6万年旅程中最为艰难的一次远征,时间为0.93万-1.3万年前。这些用骨头做成吹管吹喷出的手印,似乎在欢呼这次远征的胜利。(张振 供图)
 (相关资料图)
(相关资料图)
11月15日,世界人口迎来了一个关键节点:诞生于多米尼加的一名男婴被认定是全球第80亿个公民。联合国将这一天确定为“80亿人口日”,同时发出呼吁,建设全面适应老龄化和人口减少的社会。
距之并不算久远,此前几个10亿级的节点——70亿人(2011年),60亿人(1999年),50亿人(1987年)——我们都曾经历过,印象中联合国并没有发表过类似这样的“感言”啊。这正如媒体所评述的那样:包括新兴国家在内的诸多国家都面临少子加老龄化进程的加剧,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已成为全球性课题。也不免老调重弹:当前世界人口是不足还是过剩?是喜还是忧?
古往今来,出生、死亡和人群迁徙之间的动态平衡一直制约着世界人口数量的变化。当出生率超过死亡率时,人口就会出现增长。在平常的年份,人口死亡率大概是每年25%到35%(这个死亡率要比出生率稍微低一点),但是每隔几年,传染性疾病、饥荒、暴力冲突,或是这三者共同作用,就会导致大量人口死亡,这也遏制了人口数量的增长。
历史研究表明,在公元1700年之前的16个世纪中,世界人口的增长,大约都保持在每百年增长12%左右。公元1500年,整个世界大概拥有4.5亿人口,到了1700年,世界人口攀升到6.1亿。此后,人口死亡率开始下降,在某些地区人口出生率则出现了增长。正是在18世纪末,人口问题引起了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高度关注。1798年,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·马尔萨斯指出,如果人口增长速率超过食物供应的增长,那么将有可能爆发战争、饥荒和疾病的流行。如果人类没能阻止人口需求超出资源支撑能力的那一天到来,那么结果将是灾难性的人口崩溃。
1800年,也就是著名的“马论”问世两年之后,世界人口总数大概为9亿。及至1900年,世界人口总数已经达到16亿,100年间增长了80%。按照社会学家1929年提出的、试图解释19世纪以来发达国家人口变动情况的“人口转变”理论,随着经济发展和医疗生活条件的变化,世界人口的增长大体会经历高出生率与高死亡率并存、死亡率下降但出生率仍维持较高水平、出生率与死亡率同时下降3个阶段。
美国历史学家约翰·R.麦克尼尔和威廉·H.麦克尼尔指出,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20世纪最显著的特征之一,就是其人口发展的历史乃是一部人口骤增与锐减相互交织的历史,科学的发展与社会的变革都对此起到了主要的作用。而20世纪人口数量4倍的增长和能源消费13或15倍的增长,又导致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对环境的破坏。正因如此,在整个20世纪,人们都对人口增长给世界及其资源带来的影响深感忧虑。
这时候冒出了一个“新马尔萨斯主义者”保罗·埃利希。他因1968年推出的《人口爆炸》一书而声名大噪。在埃利希看来,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,时不时占据新闻头条的饥荒、内战和环境灾难,都反映出了人类最根本的危机。他希望人们认识到一个根本问题:地球维持人类文明的能力是有限的。同是在1968年问世、由“罗马俱乐部”委托人撰写的一份报告《增长的极限》,在当时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。它预测人口过多对环境造成的影响,将会导致大规模的人口下降。包括联合国人口委员会、美国国家科学院在内的一些机构都曾郑重预言,生育高峰将会急剧拉低世界各地的经济发展速度。
然而,埃利希等人的观点遭到了不少所谓“乐观派”的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的反驳。他们指出,在资源匮乏的时候,最大的经济收益可能来自于创新和替代性的新资源;与其相信我们能够阻止所有末日论者预测的糟糕结果的发生,还不如提倡创新,以新的方式来适应各种地球的“疾病”;要认识到人们寻求新途径、提高产量、保障供给的巨大能动性。
捧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的西蒙·库兹涅茨与丹麦经济学家埃斯特·伯瑟拉普则首次提出了乐观得多的人口论点:人口膨胀会自然而然地带来社会进步与经济增长,这不仅因为面对资源压力,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会集思广益,共同发挥聪明才智来解决问题,同时更因为,人口基数增大通常意味着会有更多天资聪颖的人物出现,从而形成更强的发展能动性,而且,人口大国也更容易发挥新兴经济的规模优势。
确实,长期以来对于人口问题,人们似乎高估了人口快速增长产生的不利影响,又低估了生育率下降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的冲击,也忽视了技术进步、效率提升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所带来的“利好”。适逢“80亿人口日”,这值得我们深长思之。

 猜你喜欢
猜你喜欢 短讯!最高反弹超80%!这些
短讯!最高反弹超80%!这些  美联储激进加息对A股和港股
美联储激进加息对A股和港股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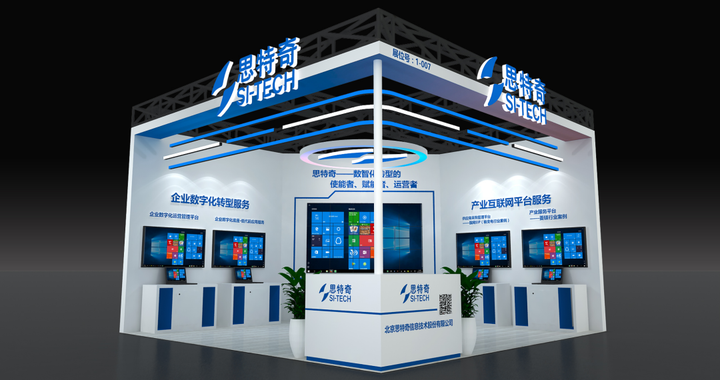 数智赋能产业升级 | 思特
数智赋能产业升级 | 思特  焦点要闻:阳光保险集团:拟
焦点要闻:阳光保险集团:拟  “AI四小龙”上市之路各不相
“AI四小龙”上市之路各不相  与用户同行!Aqara 6 周年
与用户同行!Aqara 6 周年  深圳坪山新能源车产业园一期
深圳坪山新能源车产业园一期 



